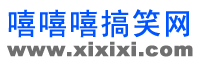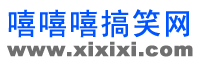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那個鬼故事需要一個冬夜的環境,現在就是。需要一個人的手冰涼冰涼,現在,我的手就是。那麼,我開始說了。你不要害怕。”
我看著18歲的男孩桃花形狀的厚嘴唇,不知道他的名字。可這不影響我們說故事。我們坐在夜行的火車上,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路上。經過無數城市,卻從不進入它們。
有目的地,卻沒有目的。
軌道代替我們選擇道路,我們無能為力,坐在車子裡的人沒有辦法推倒車子。這樣的行程,除了等待沒有別的事情可做。這是有些人濃縮的人生。
火車行駛在黑夜裡,我們拉上窗帘,因為車窗的人影虛實難辨,光影恍惚,他說,人的嘴唇都是四瓣。我便拉下了窗帘。
於是他的眼睛半垂,頭發半垂,手指間的煙頭半垂。看似安靜,象是火車的一個裝置。
“故事發生在一家醫院。”我開始平緩地說。這平緩的聲音被火車的空氣吸吮進去,聽得見,卻仿佛不是出自我的聲音。我自己都不寒而栗。
有的人說鬼故事帶著狡黠的表情,掩飾不住捉弄人的快感。有的人故弄玄虛,表情夸張,享受著被注視的表演欲,不停培訓自己的演技。
演技建立在別人的故事上,練習得越多,越會深入骨髓,到頭來,“自己”就面目全非。
現在我是一個壓抑的表演者,壓抑是因為我雖然要說一個鬼故事,可是我無意驚嚇他。故事很適合場景,我只是應他的要求,講一個符合環境的故事。我們不認識,我們同樣睡不著覺,坐在夜行車的安靜裡,想盡辦法對周圍躺倒的陌生人視若無睹。很多人脫去臟鞋。露出襪子上的洞,臭味從脫下的鞋子的大洞口、和襪子上的小洞口釋放出來,人間的味道是如此逼真。逼真在行駛在黑夜的軌道上,黑夜滅絕了視覺,視覺在黑夜裡制造幻覺,放下窗帘,閉上眼睛,脫下眼鏡。
“於是,那個人說……你的腳呢?……屍體說,被風吹走了。於是,他的腳不見了。”
我也曾在獨居的家裡,點蠟燭照出自己的臉。鏡子很小,看不到全貌。很容易嚇倒自己。或者拿手電筒照自己的臉,自下而上,效果一樣。曾經玩這樣的把戲在高中時代下鄉的時候,我們走在漆黑的田地裡,橘子散發酸酸的清香,遠處的狗在瘋狂地叫,我們玩裝鬼的遊戲,我們說,這裡的夜一點燈光都沒有。青春期的孩子。容易感傷,更容易快樂。
習慣了有燈光的夜晚。不習慣手電筒的光束,不習慣緊緊跟隨一束光的腳步,那樣就永遠走在黑暗裡。不喜歡蠟燭,蠟燭照得出人臉的恐怖,笑容猙獰,安靜最為陰森。
五指不見的黑暗,我們不曾經歷。祥和的氣氛總不會在一個人的路上。
“人很害怕,接著問:你的腿呢?……屍體說,被風吹走了。於是,他的腿不見了。”
人人都可能變鬼,而黑夜裡的光有這樣的潛力。你站在一條暗道的唯一一盞路燈下,路燈不好,不規則的一閃一閃。你就那麼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隨便保持一種什麼表情,都會把你變成一個嚇人的鬼影。
有時候我回家,要經過一條黑暗的巷子,常常有貓竄出來,沒有人家開燈就沒有一點燈光。有一次我一邊走一邊笑,我想到剛才酒吧裡朋友說的笑話,便兀自笑起來,嘎嘎嘎的,有一個人出現在前面的拐彎口,他的腳步因為看到我而騰地止住。我能夠看到他黑暗的身影的沉默中有一種被驚嚇的表情。我突然意識到什麼,而這“什麼”讓我自己不寒而栗。笑、開心、幸福、忘我,在夜裡的黑暗,和它們的反義詞一樣具有恐怖的潛力。
能夠相信什麼呢。
“人看見它的下半身不見了,非常害怕,可是禁不住繼續問:你的身體呢?……屍體說,被風吹走了。於是,它只剩下了頭和雙臂。”
人人都可能變成別人心中的鬼。
夜行車有種讓人鬱悶的節奏,無論快慢,均勻不變,死氣沉沉。因為我們看不見窗外經過的城鎮,我們有理由想象窗外什麼都有可能發生。黑暗包容一切,縱容一切。本分的生活被掩蓋,欲望被掩蓋,血液流淌,夢境外溢,兇器也不再看得見,善良也不再看得見。
幾千公裡的鐵軌上,我們默默坐定,在無數城市中間一閃而過,誰也來不及看誰。時間有限,你我匆匆。
“人好奇而驚恐,看著怪異的軀體問:你的頭呢?……屍體說,被風吹走了。於是,它的頭和臉都消失了。”
有人喜歡在別人的容顏上找到愛和信賴的立足點。容顏蒼老的過程中,希望感情隨著皺紋刻入身體。有人喜歡看著你,就那麼一動不動地看著你,直到你心虛。一切秘密盡在眼睛這個洞穴裡,最可怕的就是空洞,輕易的,你進去,卻再也出不來,你大聲叫喊:開門開門!可是它就是不眨一下眼睛,你看到世界變成你無法染指的電影,你成了別人生命中的一雙眼睛。你的身軀四肢心臟再也沒有機會碰撞別人的身軀四肢和心臟。
18歲男孩的臉依然半垂,他的煙落下一截灰,他的眼睛鎖在空洞的某一點,聆聽,在他的想象裡。我,表演,在我想象裡。
“最後,人看著唯一剩下的雙臂逐漸消失,他緊接著問最後一個問題:你的手呢?……屍體沒有說話。”
停頓兩秒,仿佛故事和現實需要一點時間溶化在一起。
我那保持緘默的身體突然發作,把冰冷的雙手扣住他的脖子,他的脖子很細很細。
我無意恐嚇,那只是一個鬼故事。故事需要表演者身體力行。
男孩不再是一個裝置,他跳脫我的手,雙手肆意揮動,要趕走我的手。我看見他的臉,鬼一樣可怖。
我們兩個在車箱中,被我們的叫聲驚嚇而醒的行人茫然地看著我們,我們旋即坐回原座,不知道該接下去說什麼。這使我們看上去象一對陌生人,逃避著對方的眼睛,如果碰撞到一起,我們都認定自己撤走了眼睛裡的東西,不給別人一丁點提示。
實際上,從此我們保有了一個秘密,我們的恐懼達成了統一。這是默契的一種。
風一定是有的,因為車子行駛得如此飛快,路過每一座陌生的城市,我們坐在車箱裡,象軌道上的一個裝置。不知道誰先變成鬼,不知道誰進入了誰的眼睛、還有感情。
一切都是偶然,並非蓄意並非惡作劇,甚至還帶著體恤、憐憫、理解、歉意和滿意。和愛人、和路人、和仇人,這樣的默契隨時可能發生。
一雙手,一個眼神,一句話,無意間,都是黑夜裡的光。
·上一篇笑话:
13岁那年发生的鬼事
·下一篇笑话:
灵异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