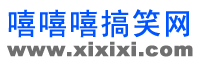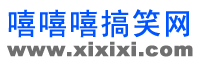我叫鱼,我和虾是一个旮旯里的耗子。我们的交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原始社会真是好,人人光腚到处跑——光屁股的年代。那时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的就是尿尿和泥捏手枪;再大一点,就是从洋槐树上捉了毛毛虫放到小女孩的脖子里;更大一点呢,那就是白天爬到楼顶上,向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撒沙子,夜晚则往下尿尿。及到学龄,则一起逃课,一起打架,一起抽烟喝酒,一起去录象厅看录象,一起去游戏室打“魂斗罗”,一起泡妞——泡同一个妞,乃至一起被数次勒令退学。
那时我们有一个外号叫“黑风双煞”,当然不贴切了,看过“射雕”的都知道嘛,可人们就是喜欢这样叫,我们也他妈的没办法。老师对我们的评价是:把牢底坐穿。这完全是扯蛋嘛,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进过几次看守所,但那是拘留,不是拘役。还有一个评价嘛,哈哈,是我们所得意的,只是不好说——那个老师已经因为反革命被判刑了,其实在他对我们的评语里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只是那时我们年纪尚小,政治敏感性不高,白白失去了一个为国立功的好机会。他说我们长大了不是当个黑帮头子,就是做个XXXX人!了得呀了得!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预知未来。我们没有经受牢狱之灾,也没有成为黑帮头子,更没有做XXXX人。我们像大多数人那样娶妻生子,过着平凡而逍遥的日子。如果不是虾不听哥们劝阻娶了一个爱吃醋的泼妇,一切几乎可以称为圆满的。
该死的愚蠢的虾!
食色性也,圣人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向芸芸众生揭示了人性之真谛。可偏偏就有些专制的蠢女人拼命的压制我们的人性,结了婚后就把我们像看门狗一样牢牢的拴在家里。
虾一回到家,他老婆就像机警的警犬一样窜上去,把他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嗅个遍,倘闻到半点异味,就大吵大闹一场。虾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独独怕老婆,唯唯诺诺,屁也不敢放一个,真是一物降一物!我数次给他做工作:“离了吧,哪里还找不到个老婆,受这罪干嘛!你不是对我那口子有贼心吗,我割爱给你!”他的眼珠子贼亮一会,又灭了:“等等再说,等等再说吧……”我又给他出主意,“不行我去教训教训她,灭灭她的威风!你一夜夫妻百日恩,下不得手,我和她没这事,可不尿她那一壶!”他犹豫半天,兴奋起来,攥攥拳头可又松了,说:“算了吧算了吧……”
我四处给他买药吃,什么汇仁肾宝呀、大力神丹呀、九转回春丸呀,甚至连甲睾酮片都吃了,他就是不来男人的脾气,白白糟蹋了我仨多月的工资。
唉,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这小子既然不听兄弟的,那就让他吃点苦头。我到朋友那顺手牵了一瓶六神花露水,瞅这小子不留神就往他身上喷一下。哈哈,晚上就有交响乐了听了,中央乐团的‘黄河大合唱’也不过如此。顺便说一句,我和他是邻居——就像朝鲜和咱祖国的关系后来大概虾婆发现了我的诡计,也或许是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制越来越健全了,吃醋也开始讲究证据了。她不再闻虾身上的气味,而是找头发丝。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就唆使虾留长发,这样的话,发现了长头发也可以面不改色的说是自己的。可还没等虾的头发留起来,就给虾婆用剃须刀刮了个溜光!
人说男人结婚之后就不再有朋友,女人容不下丈夫的友情。果然不错。虾开始慢慢地疏远我,后来干脆躲着我。
这天下午我提前半小时离开办公室,来到虾单位的门口等他。我坐在马路的栅栏上,点了支烟,慢慢地想,想着我们哥俩二十多年的交情,和现在凋敝的友谊。我的怒气越来越盛。这小子出了大门才看到我在栏杆上坐着,他低着头想装做没看见。我把半截香烟掷到地上,迎面走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衣领把他摁在墙上。
“你小子怎么了?娶了老婆忘了兄弟了?你忘了当初你挨砍谁给你挡刀了?你忘了你得罪了人是谁替你吞玻璃了?你忘了是谁大冬天把大衣卖了给你凑钱让和你那该死的老婆去泡吧了?”说着说着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不住得用手抽打他的脸,“你小子看现在你这熊样,还是男人吗?我打死你得了!”我狠狠的揍他,他的鼻孔里嘴角都出来了血,我仍不停手。人们远远的看着,没有一个敢来劝架。
他忽然抱住我,“别打了别打了,我听你的还不成吗,”他哭着说,“咱哥俩这就回去休了她,让她滚蛋,咱们永远是好兄弟!永远是!”我也抱着他,两个大男人在大街上大哭起来。进了他的家门,我觉得气氛忽然变了。
虾婆不屑的乜了我一眼,径自走到虾的身边,问:“今天怎么回来晚了?又和谁鬼混去了?你的脸怎么了?你说呀?”
“让我打的!虾,你不是有话对她说吗?”我冷冷的回答。
“我……我……鱼,你……你先回去吧……”虾可怜巴巴的说。目光游移着,不敢和我对视。
一时间,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虾婆开始翻看起虾的衣服来,看样子是没找到半根头发。可忽然之间,她号啕大哭起来:“天哪,现在连女人也有秃顶的了……”
面对虾婆的无理取闹,虾吓得脸色都白了,一声也不敢吭,只哀求的望着我……
我和虾决裂了。
·上一篇笑话:
不好色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下一篇笑话:
猪八戒害怕洗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