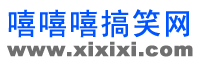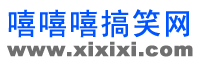我死的很悲壮。
……,
◎_ㄓ╃eξγ
……
(对不起,我一激动就会写些乱码出来)。
我死的悲壮。
我死之前已经懂得了许多事儿,这对我不容易。
现在我不能再拉出诗歌一样的丝网,就借我早就知道它叫做笔的东西写给你们。替我写字的人和我有些渊源,不然我就不会折腾他夜里不睡趴在桌子上写,这很难为他,看见他的字很难看,我就知道他的质量也许还没达到高中生的水平。
我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家。懂事的时候我已经住在这里好久了。我因为喜欢这里,就从来不走出去见太阳。我的家很规整,窝儿大体就是三个大的平面呈九十度角结合在一起那个地方。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里大概能有八个这样的大气的连接点,另外也会有很多小的这样的连接点,我不喜欢小里小气,从不去那些地方逛。走出大厅的门,走廊还有这样八个地方,从走廊进厕所或者进厨房,都各有八个这样的连接点。我懂事以后就觉得往下看的滋味好,于是我选择的落脚处,都在上方。
我小时候很丑,并且我不知道我能长多大的个儿,更不知道我会不会一直这么难看下去。从前这房里的那个老处女每次见到我都要大叫起来,我就赶紧走开几步,回头看她还惊歪歪地瞪着我,我怕她发神经用拖鞋拍上来,只好荡着自己的丝,尽量把那个连接点瞄准了,每次都争取一次荡回家以防不测。好在老处女一次也没打我。后来住进来的这个女孩子比原来的老处女忙,好久也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也不讨厌不打扰她,夜里她开灯时我曾经紧张过,发现她不是注意我,就也不再紧张了。那天我在厕所里正背诗歌,女孩子进来一眼看见了我荡在便池上方,她十分温柔地叫了一声“哦呀“,说小家伙你在干什么呢,你掉下来就会淹死了。她伸出手接住我,又捧在面前笑容满面地端详我,然后把我轻轻地放在墙边儿,我当时吓的够呛,怕她也惊叫也恐惧也会找个什么东西打死我,她这等温情地打发我,叫我心里一下子产生了有生以来头一次的不平静,我三步两步一回头,她大小便全完事儿了我还没走回自己的角落,平常这两步道儿我最多用一分钟时间就能走完。
这个女孩子的手真好看。白白嫩嫩,温度很好。她说话也好听。我在她手心里爬,小心翼翼地爬到她的手背儿上,她就翻过手来继续看我。她说小家伙你真可爱呀,还说早报喜夜报财现在是早晨你是要给我报喜呀,还说今天要办的事儿正是喜事儿呢。
她说,小家伙你的屁股上有个红点点儿耶!
我回到自己的窝窝儿,躺在自己织好的丝网上,用力地搂过自己的屁股看。呵呵,真有一个红点点儿呢!那个红点儿只有针鼻儿大小,难为她怎么看得见!
ь┏△︿э,δω⒌なǒ⊙∮■……
我的身体由浅褐色渐渐变成了黑色,屁股上针鼻儿大的红点儿可一点儿也没长。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成年,而身体可能就永远这么大了。我知道了我是属于这小型的品种。我懂的事情多起来。每天拉丝也开始有了区别。我懂了我要靠它行走自如在窝里和别的什么地方来来回回用的丝要使劲地弄结实,粗点儿保险;专门用来结网粘个小蚊子、蠓虫的丝要很细才行;窝儿口的地方要弄些防备别的什么虫子进来的保护丝要多抻拉几次,越紧越好。还有一种我经常拉的丝,细细的松松的还有点波浪纹,这就是我写的诗歌。这波浪型的诗歌没有实用的任何功效,可我一闲着,尤其在心情好的时候闲着,还尤其在看到房里的女孩子慈爱地注视我的时候,我就喜欢拉这诗歌。
这个女孩子爱干净,也三天两头地打扫屋里的犄角旮旯。每次打扫到我的丝网上,她都不忍挥手扫净我的诗歌。她不知道我的那些丝网是没有用的,她以为我要靠那波浪型的诗歌抓蚊子吃。后来我就尽量不在最漂亮的大房间里做诗歌了,我想把拉诗歌的地方固定在走廊的背光角和厕所的几个清净地带。我不愿看到女孩子为我为难。
女孩子有一个男孩子,我说的是能在一起睡觉的那种。我听他们聊天时猜想就是女孩子第一次见到我说她“要办的事正是喜事“那天他和她认识的。女孩子对男孩子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我会爱我,因为我去和你见面的那天早上看到了喜蛛,而且喜蛛的屁股上还有个红点点儿。她说的那喜蛛是指我。人们把很小的、没有肮脏感的蜘蛛都规划为一个称为“喜蛛“的品牌。
我们在一起享受了一个下午。我说的是我们,我和那个女孩子和那个男孩子。他们弄了好多吃的喝的,凉的叫冰激凌,热的叫咖啡,干的叫薯片面包,湿的叫草莓果冻。那男孩子打开电视机看动物频道,女孩子戴上耳机听一个薄薄亮亮的圆盘盘。我荡着秋千爬在他们坐着的沙发后面,试着自己要融合进人类生活,心想要是融合不进去也至少能凑凑热闹。女孩子发现了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和和气气温温柔柔地叫我“哦呀小宝贝你也来啦“,还是伸出好看的小手让我爬上她的手心儿。她嘻嘻笑着挪动角度看我屁股上的小红点点儿,并色迷迷地指给她的男孩子看。男孩子看了,说我不是普通的喜蛛,至少也是个杂交二代品种,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则是美洲最毒的蜘蛛“黑寡妇“,就是能咬死一头牛或者一个人的凶狠蜘蛛种族。女孩子说不是的,你看它多小啊又这么老实,屁股又那么可爱,怎么会有毒。男孩子说屁股上的红点儿正是“黑寡妇“的标志。女孩子就有点害怕了,把我放在地上对我说那你走吧,又有点舍不得,就把头伸下来把屁股撅在沙发上看我。我不爱走,赖在地上不动。男孩子怨女孩子只是看我不看他,抬脚要把我踩死,女孩子就急眼说你干什么你狠打了男孩子的腿。男孩子就呵呵笑,一头拱在女孩子的屁股后头,说你看“黑寡妇“屁股,我就看你屁股。女孩子回头给男孩子一巴掌,然后就一头钻进男孩子的怀里,亲他的嘴,又扒他的衣服,不顾弄了一地的冰激凌,使劲儿地贴在一起。他们不老实的时候,我悄悄去用长脚沾了一点儿地上的冰激凌,这白白的粘稠的东西把我冰的打了冷战,可我还是忍不住揽在嘴里尝了尝,真是美味啊,甜的钻心。我美的自己又想拉些诗歌出来,可在地上没法施展。我就伴着女孩子和男孩子做爱的好听的刺激的看起来要持续很久的呻吟,从墙角儿向上,向上,爬到我的角落,忘记了我不该在这个房间拉诗歌的约束,颠着接近舞步一样的节奏,看着下面人们的情欲,拉出了我尝到冰激凌后有点儿战栗的诗歌。我记得诗歌的大意是:
★βǒuщ冰激凌@◎◎︿ぉ
姑娘∥ψǐミ─▲#
んτθθeⅣβξ☆★交配△▲
#□ㄎㄞ〖oǒ黑寡妇я※
……
人喜欢把不是人的东西都尽量想象成和人一样,对蜘蛛也一样。女孩子和男孩子谈论蜘蛛有毒的话题,还引来了不少我没听说过的东西。他们分析我是怎么会来到家里的,女孩子说是阳台飘进来个干树叶儿上面有个蜘蛛蛋;男孩子说是原来的房客喜欢养花儿挖回来的土里有个婴儿蜘蛛。女孩子说电视里演的蜘蛛交配后一个把另一个吃掉;男孩子说爱情的本质就是要两个融在一起,人也是,蜘蛛也是。女孩子说你讨厌你讨厌你要把我吃掉吗?男孩子说要是吃掉也是你吃掉我,蜘蛛都是母的把公的吃了。女孩子说母的怎么这么凶连爱情也不顾啦?男孩子说公的个头儿小斗不过母的。女孩子就开始往天棚上看,说咱家的喜蛛一定是个公的它那么小。然后推推男孩子说你说你说这个小红屁股一定没有毒,我看它不能有毒,我看它可老实呢。男孩子说天下的蜘蛛都有毒的,只是红屁股的爸爸妈妈毒大,红屁股是杂交品种,毒可能小些。女孩子说那它也可能没有毒,男孩子说那也可能它的毒比它爸爸妈妈还大!
我就在屋里的上面的一个墙角趴着,听他们说话。我老是通过听听看看丰富自己。但蜘蛛不太会分析,看见的和听到的就记住了,记住一个就是一个,不太懂电视一定要通电才能看,不太懂睡觉后一定会醒来,不太懂人的很多做法为了什么,因为蜘蛛做事不想为什么,到什么时候就会自然地做什么。我每天都在学问上能进步一点,比方这次,我知道如下内容:
我最小的时候是个蛋蛋;
我一定是有毒的;
我是公的,将来我和一个母的交配,我就会被那家伙吃掉;
还有下列思考题:
爱情;
女孩子听的那个光亮的圆盘盘儿。
房间里填家当了。最先搬进来的是一张又宽又大的床。在这之前我一直频繁地在换睡觉的地方,一阵子在厨房里,一阵子在厕所里,因为女孩子把每个房间都粉刷了一遍。原来的墙是白色的,刷完后变成了浅粉色。男孩子进来看看说这个颜色很温暖。搬床的那天女孩子累的满头大汗,她大声指挥着搬运工,大声训斥他们毛手毛脚。摆好了在屋里的位置后,她就仰面朝天地往床上一躺,我正好看得清她的表情。她眼睛里放着光芒,自己一个人傻笑,又抱过来枕头贴在胸口和脖子那个位置,发神经一样地亲吻那个枕头。然后我看见她又一下子跳起来,去走廊把小背包拿进来,打开,捧出一个书本大的镜框,先是自己美孜孜地端详一番,再把镜框立在床头的小柜上,再退几步远远地看,把头向左歪了歪看,又向右歪了歪看。嘴里嘟哝说就是小了点儿,就是小了点儿。
那镜框里是张照片。女孩子和她的男孩子的照片。
我听见女孩子的女朋友们来做客说的一些话,她们喜兴的样子是在讲一个叫做“结婚“的新词汇。我听不懂,加上我也为睡觉的地方折腾了好多天特累,就不去瞪大眼睛听她们说话,顾着自己休息。我这几天都没拉诗歌。
我的脑袋很小,肚子相对地很大。我的分析功能集中在脑子里,怎么也发达不起来;我的记忆功能全在肚子里,能拉多少丝就能记多少东西。我拉出的丝就是记住了一遍什么东西,再把丝吃进去再拉出来,就又复习了一遍。我一直在不停地拉丝和吃丝,除了那些我不在意拉的诗歌算我的排泄物外,我的吐纳生活等于学习学习再学习。但一般一个新词汇能引起我的敏感,不知怎么“结婚“这个新词儿我觉得不能打动我的学习神经。初步的理解我就把这个词儿暂时和女孩子讲卫生放在一起了。因为女孩子一直在收拾房间,看不见男孩子来收拾,而女孩子收拾屋子是要结婚,那么结婚就是女孩子讲卫生。
蜘蛛是需要一点潮湿的。厕所的潮湿度很好,我在那里的滋味最滋润。马桶的水箱里常年有清澈的水流,大大的浴盆儿里时常会弥漫着潮忽忽的热气。女孩子喜欢把身子全都浸泡在水里,并不象电视里演的那样水面上弄一层泡沫,而是干干净净的水,能看到女孩子全部身体的水。女孩子会在浴盆儿里哼哼叽叽地唱歌,她一唱歌我就想拉诗歌,可拉诗歌会耽误我看她,我就不拉诗歌拉一条长丝把自己吊在半空荡来荡去。女孩子好几次都发现了我,她和我说话。她说小家伙你看来不怕水啊,小家伙看起来你会游泳吧。她试着把我接在手里,拿过个香皂盒儿接了凉水,把我放在香皂盒的凉水里,再把香皂盒飘在浴盆儿里。我开始坐船。人们老是说在大海上看太阳早晨出来时是个享受,我没见过大海也没见过太阳,只是在电视上体会过那些电视剧里的情节。我感觉我这个时候就是在大海上,那太阳就是女孩子的脸,那太阳光在海里的照射就是女孩子的水里的身体。“船“里的冷水被“海“里的热水加了温,我有点吃不消,就爬在了“船“的边儿上。女孩子就说我哦呀小红屁股你好流氓啊,这么贪婪看女孩子的身体。我发懵她说的话,不懂。她就拿起香皂盒把我放在了浴盆儿边上,站起来,跨出水,拽了个毛巾围在身上,回头指着我说,我的身体是给最爱我的人看的,你不许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能看我的红屁股,我不能看她的白屁股,我就愣在浴盆边上,“大海“都“干“了我也没走。
我得定期吃些食物。拉出的丝网反复咀嚼没有味道。女孩子的房间里有蚊子,她老开窗户通空气,蚊子就进来了。傍晚我在床的上面的窝儿口拉了个很小的网,心想就一个晚上,明天一早我就把网吃掉,不让女孩子烦心。网均衡地拉在三个平面上,位置很美,网丝辐射的也好看。我想女孩子的粉色的房间好干净,我拉的丝网也一定要漂亮才能对得起这个房间。我趴在三个平面的连接点上,丝网离我只有几步远,我要是一跳,就能马上“飞“在网上。
女孩子的鼾声象唱歌一样好听。可这个新床不太好,女孩子翻身时它就响的跟放屁一样难听。我想伴着女孩子的鼾声一起睡觉,床的声响叫我一会儿一醒地睡不安宁。
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女孩子突然开了灯。她跳起来打蚊子。那蚊子一定咬了她,我看见她十分气急败坏。蚊子倒霉,偏偏逃到了我的网上。这个蚊子是吸饱了女孩子血的,它的身体已经膨胀,力气也很足。它不服气粘在我的网上,挣扎的很厉害,我的丝网被它弄的左摇右摆。本来我很少直接去攻击刚落在网上的食物,都是等天亮的时候去收拾战利品,可这个蚊子再挣扎下去很可能弄破我的丝网,它把为了配这个房间而专门设计的十分规矩的丝网弄的破烂不堪,我只好出击。我以最快的速度飞身上网,用四只脚按住了这个不老实的家伙,用两只脚拉出硬丝捆绑住它的身体,探出毒牙狠狠地掐在它的头颅,把力量从我身体的最后部分向前猛力集中,毒液几乎是在蚊子的身体里喷注……挂在网上的只有我的两只脚了,我的愤怒让我差一点儿跌落尘埃。
女孩子的眼睛就在离我咫尺的地方。她惊讶地看着我,有点儿恐惧,有点儿幸灾乐祸,有点儿莫名其妙。女孩子看见蚊子已经不动,看见我的肚子还在激烈地起伏,就又轻轻“哦呀“了一声。
她说小红屁股你可真厉害呀,小红屁股你替我报仇雪恨啦,小红屁股你很凶残啊,小红屁股你真有毒啊。她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小红屁股你怎么从来不咬人呢,你看你和我玩的时候多老实啊,嘻嘻你是不是爱上我了不咬我?嘻嘻你是不是因为要住我的房子而不敢咬我?然后女孩子没睡觉,关了灯坐在床上发呆。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她自己对自己说话,她说你说爱我就来住这个房子呀,象这个小红屁股一样啊。
这最后的话我没分析出来。但我知道女孩子说的“爱“就是爱情那个“爱“字儿。
我没吃蚊子,累了睡着了。临睡前我编排了一下我今天的记忆:
爱情;爱;互相看身体;住她的房子……
女孩子一个人住久了没有什么人来,我就想起先前住在这里的那个老处女。我怕女孩子也变的苍老和神经习习。所以我也盼着那个男孩子来和她说话和她做爱,还盼着男孩子来时我能再一次看见女孩子听那个薄薄的亮亮的小圆盘儿。我记得女孩子把圆盘盘儿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就戴上耳机摇头晃脑地样子很享受。那个圆盘儿反射照进来的阳光曾经映在我身上一次,感觉很温暖,我在那一刻曾闭上了眼睛体会。男孩子走时拿走了那个小盒子,忘记的一个亮圆盘儿在桌子上。可惜女孩子没有了盒子就不能听耳机了。
我也盼女孩子也盼,男孩子就来了一次。但来了两个人坐的不那么近,也没紧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也小了,而且老半天才说一句话。女孩子告诉男孩子,她给他买了套西服,是他最喜欢的浅灰色;男孩子说浅灰色不流行了,现在流行浅蓝色;女孩子说你试试看,男孩子说别试了怪热的。女孩子坐在床上一会儿按按床垫软不软,一会儿摸摸床腿儿光不光;男孩子坐在沙发上一会儿玩玩儿打火机一会儿看看手表。然后男孩子站起来要走。女孩子就送他到门口。我听见他们在走廊里说了好几句话,还听到有声音象是他们在拉扯。然后就是开门的声音,女孩子还在说什么,男孩子有脚步声就走远了。
女孩子回来后就不高兴,把脸埋在床上。一会儿,女孩子发了神经,抓起枕头随手扔在地上,坐起来又拣起枕头抱在怀里。她看床头的照片,上面的两个人依旧笑容满面。我又想起了老处女,老处女也有过一个男人,我那时侯还小,不懂事,但我能记住在老处女家里再也没来过男人之前,在老处女家里来过一个男人之后,老处女就和现在的女孩子差不多,当年砸碎了不少东西呢。对了,我懂得什么是处女,就是女人没和男人交配过,现在我用新词儿叫做爱。老处女和那个男人没睡过觉,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她一定是处女。
动物凶猛。我属于动物。我凶猛。我在蜘蛛的文化里老是要融合人的文化,因为人能弄出那么多好看好玩儿东西,我佩服人。人不凶猛,老处女和这个女孩子都不凶猛,那个男孩子也不太凶猛,我乐意和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也不该凶猛。我不该那天露出牙齿疯狂地捕杀那只蚊子。我在女孩子面前露出了我本来的凶残,我不应该。蜘蛛到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这个性格要改变才好,要改的象人似的到什么时候好象没在做什么。女孩子说那叫“渐渐“,或者“隐瞒“。这两个词儿又是她和来访的女友说话时讲出来的,我似懂非懂。她们例举的事实是那个男孩子的作为。那天女孩子给她的女友讲了我抓蚊子的故事,她说我家的小红屁股象个飞侠呀,那动作就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似的,一下子就把蚊子给掐死啦。记得她的女友骂了她,说她神经病,说整天玩个破蜘蛛,那东西谁家没有几个,脏习习的。女孩子说小红屁股可不脏,既安静又忠实哪也不去就在家里陪着我。女友说你恋上了红屁股啦,怪不得人家不来了,他怎么能忍受你和蜘蛛产生爱情?说完就嘻嘻哈哈地笑。女孩子也就不说话了。这段时间我不爱波动自己的情绪,有点儿懒塔塔的,但她们说的乱七八糟的话我就禁不住瞎想,我想那个叫“爱情“的新词儿大概意思是在一起住加上互相看身体加上做爱或者叫交配,在“爱情“时要听亮亮的圆盘盘儿和吃冰激凌。那么我分析我和女孩子还有几点没做到,一个是听那个圆盘盘儿,一个是交配。我又分析了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性,第一,我有可能爬在耳机上听听圆盘盘儿里的声音;第二,我是公的,女孩子是母的,交配有可能发生。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想把自己变的不再凶残,而女孩子却有点特别夸奖我的凶残。我吞咽自己的丝,我继续学习。
家里已经好几天没有人了,女孩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有女孩子在家的头一天夜里,我觉得安静的有点儿心旷神怡,就又再走廊里厕所里拉开了诗歌。我拉了一个很长的诗歌,内容梗概是关于第一次和冰激凌接触的体会。我把自己最好受的滋味都拉进了诗歌里,包括一些关于我英勇的美洲双亲和我侠客般的身手,还有我把我的红屁股想象成健壮的阳具。天快亮的时候由于我打瞌睡,从诗歌中掉到的现实中,摔在浴盆儿里,浴盆里没有大海一样的水,幸亏有一盆儿没洗的衣服接了我,软软的没受伤。那衣服是女孩子的内衣裤,还有女孩子好闻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我一直在等开门的声音。没有。
第三天还是没有开门的声音。
第四天我在厨房散步,看见有个老鼠在地上也在散步,我好久没有见过老鼠了,本能地立起腿脚,抬高自己的身体做战备状,还探直了自己的触角,差一点儿就亮出了毒牙。老鼠其实离我很远并根本没答理我的存在。我后来哑然地觉得自己真是大可不必。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我完全相信我可以象侠客一样地把老鼠一口咬死,我的毒液是美洲遗传过来的,曾毒死过一头牛。
&☆☆§ㄘъф●↑▲,
ま\※★◆eǚoooooσ ̄ ̄◎……
想起来我就发抖。抖的时候很想把自己的毒液注进自己的臂膀里,那毒液是很能使自己麻痹的。可惜我已经死了,没有毒液了。
我死的很悲壮,我死的实在是很悲壮。
女孩子回家了。我在她的房间的门框上,听到开门声我探头看见门开了她进来。她把背包放在鞋架上,对镜子照了一下自己,用手抹了一下脸。她走进屋子来,坐在床上,然后又站起来找了个香烟,又找打火机。点上了抽一口再吐出来,她的嘴唇不安静地动,手指也发抖。我看清了她脸上不那么干净了,眼睛下面有些不好看的黑色,眼睛也没有原来好看了,但好象眼睛长大了。我心里想,这女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啦,大概该洗澡了。我回过身,准备去厕所等待女孩子洗澡时我陪着她。可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嚎叫,吓的我连忙缩紧了身体。在我弄清这哭嚎声是女孩子发出来时我才转过身体看她。她已经伏在床上大声哭了,香烟头深深烫在床单上,烫了一个黑洞,大概熄灭了但焦糊味儿已经弥漫起来。女孩子双手抓住床单把脸捂在被里闷声哭叫着,两腿也乱蹄了几下,把拖鞋甩出老远。一会儿,她又坐起来,呆呆地看床头上那张照片,突然一拳把小镜框打飞了。然后又是哭,不太出声地哭。这次哭的时间长,她不搽眼泪,我能看见她的眼泪从她下巴上落在地毯上,一滴,一滴。
这分明是受了很大的委屈。这分明是这些天她一直在受委屈。我不知不觉地往前爬着,想靠近她,想让她发现我,想象着她一见到我就会叫着“小红屁股“开心起来。
她没有看到我的存在。她站起身来开始找东西,先是找到了一个太阳镜,然后找到了一条领带,她又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套浅灰色的西服,还拿来了一个剃须刀,最后从桌子上拿来那个亮亮的用耳机能听的圆盘盘儿。她取来一个铁盆,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了盆里,用打火机点着了。房间里一下子充满烟雾,棚顶上也开始热起来。我感觉大事不好,可又不忍扔下女孩子,就飞快地从墙上拉个丝落到地上。烟雾中女孩子站起来打开阳台的门窗,烟雾里女孩子继续流她的眼泪,烟雾里女孩子从火盆儿里拿出那个圆盘盘儿端详了一会,再一下子把它掰成了两半儿,烟雾里我看见了圆盘盘儿划破了女孩子的手,手指头有红红的血迹。
房间里的烟雾散尽时已经是傍晚了。女孩子在喝酒。她喝的酒是红色的,不是原本就是红色的,是她自己弄成红色的。她先把一罐儿番茄汁倒在杯里,再加了一点儿盐面,就用电视广告里介绍的那种“伏特加“酒冲在杯里。她喝了不少,喝的很热。她脱了外衣内衣,最后连什么都不穿了,就象她在“大海“里那样。
她终于看见了我。她把我接在手心儿里,还是转来转去看我的屁股。她和我说话,那酒味儿很难闻但我坚持着听她说。
哦呀小红屁股你来啦,哦呀你来陪我吗,哦呀我喝了好多酒啊你喝不喝呀?哈小红屁股你又看见我光着身子啦,你真是流氓成性啦,你看见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受啊?你看我是不是很好看呀,你看我的乳头象番茄汁儿一样红呢,你看我的屁股和你一样美呢!小红屁股你知道我喝的是什么吗?这东西名字好听耶叫血腥玛莉,味道怪怪的可舒服啦!你知道吗,就是在厕所见到你的那天晚上才我才知道这种喝法呢,是他告诉我的呢,那天我们第一次约会啊,他说心情不好就要喝血腥玛莉这样的烈性酒啊。他哪里知道我自己也能配这种酒喝呀,他看不起我喽,他玩够了我就不爱我啦!他找到大房子就不要小房子啦,他不知道什么是爱呀,要我就爱啦,不要我就不爱啦,他不懂呦!还是我们小红屁股好啊,知道爱我,也知道我爱你,天天守着家,天天看人家洗澡光身子,是不是啊小家伙?还有啊,你给我报仇雪恨吃蚊子啊,简直就是一个英雄救美啊,你要是个男人啊嫁你幸福死啦!啊哈哈对啦,你是公的啊,是个男子汉哪!啊呦你就娶了我吧?啊呦娶我好啊,要不然你和别的红屁股结婚她会吃掉你的,她让你干一次就吃了你,再去找别的红屁股干一次啊再吃一个,我不吃你啊,你有毒啊!哦,你有毒啊,你有毒的……
她又重复,你有毒的……
我的反应来不及了。她说啊说啊,一直在嘻嘻哈哈的,我被她的酒气熏的大脑有点儿迷糊,最后她说我有毒然后再次重复我有毒时,她的脸上已经起了变化,她在片刻间想到了什么,我只看到她的表情一下子好象庄严起来,那庄严中带着恐怖。我感觉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可晚了。我的英雄救美的快速壮举远远比不上人的思维和动作的敏捷,女孩子已经一把抓过我,翻手扣在了酒杯里,又快速地浇进几滴番茄汁儿,然后把伏特加酒狠命地冲进酒杯……
我在酒精的急流中翻滚。周围是鲜红的颜色。就象我屁股上美丽的斑点一样颜色,就象女孩子圆圆的乳头的颜色,就象她刚才掰开圆盘盘儿划破手流出的血一样颜色……伏特加溶掉了我腿上身上的油脂,浸透了我身体里学了好久的人类文化,开始蒸发。我感觉到了她把我倒进嘴里,感觉到了她舌跟儿的痉挛,感觉到了蠕动和烧灼,感觉着被母蜘蛛吃掉的快乐,我想拉出我最后的有题目的诗歌,诗歌的名字叫:“为爱献身“。
@→§疼§终止щ〃,
ま▲ ̄爱情\▲,
凶残人¤°¢‰‰,
■☆★☆未知★3¥↑。
……
我死了,灵魂没有被蜘蛛阎王接纳,因为我满身酒气和满脑子的人的思想。我还是尘缘未了,想继续修行下去。我记得临死前我似乎弄明白了什么是“爱“和“爱情“,但没有归纳出来简单的概念。我还迫切想知道女孩子听的那个圆盘盘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对我没有意义但我习惯了没有意义的探索。后来我象灰尘一样飘啊飘啊,竟然飘到了女孩子的那个男孩子的家里,在这个男孩子的房间里我看到了有一大堆亮亮的薄圆盘盘儿,还有那个方盒子和耳机。伏在耳机上听了听,觉得里面就是音乐没有什么特别。我开始反感人类,就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儿。我想有音响,有电视,干吗还要用这个耳机听圆盘盘儿?哦,学会了那叫CD。后来发现了个区别,音响和电视是大家共用的,而这CD和耳机只能一个人用。我确定我对人的印象开始恶化了。
男孩子和另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我从此也明白了“结婚“这个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感兴趣的词儿。他们也吃冰激凌也交配也嘻嘻哈哈。我看着来气,心想他一定忘记了那个为他而死的女孩子。我集中了我的魂魄,运用了人类文化中冥界的旁门左道,将自己的灵附在了这个不义的男孩子身上。我让他写,让他莫名其妙地在我的控制下写,反正我是孤魂野鬼,我才不怕什么附体会有恶报应的清规戒律呢。
鬼魂附体一定没感觉,这小子不知道自己的灵魂被我借用了一下。可小子一直觉得自己近来的恍惚。我带小子去喝“血腥玛莉”,他发愣地看杯里的红色,我就是要点化他,叫他时常看见红色,在喝水喝酒喝汤喝药时都能看到红色,甚至我想叫他在血腥里看到我,一个蜘蛛。
·上一篇笑话:
央视10大XX体育主播
·下一篇笑话:
免费获取Q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