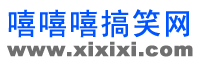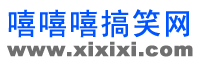天下大乱。闲雨敲窗,吾辈之人惊呼,——这次第,唬煞我也!
所有的语言被颠覆的踏在脚下,只要标新立异已经不管周围数倍炽烈的眼光如炬,你有你流氓他有他痔疮,我们还剩下什么?
满街的乳房奔走匆忙,行色匆匆,雄性动物们光着腚挥舞着手中的三角内裤,急急加入这流氓或者痔疮的队伍之中。对面高高的擂台之上,一个须发皆白面容慈祥的老者安静地演讲,“当下雨的时候你会想起雨伞,痔疮来临之时,你会想起什么?”下边所有奔走的雄性雌性雌雄同性们,站住高呼,“我们是流氓!因为流氓,所以前卫,因为流氓,所以先锋!”老者依旧不慌不忙,态度和蔼,“为什么要流氓?”所有人用不屑的眼光看着老者,“还号称文学大师呢,流氓代表着如日中天代表出名代表人民币都不知道!”
我在角落观望,不敢近前。
老者看到了我,走近前来,拍拍我的头,“孩子,其实他们不是流氓,伪流氓而已。”
我都知道,可是这些伪流氓们已经挥舞着改革的大旗进行着翻天覆地的颠覆了,真流氓来了该会如何?吐沫已经满天飞舞,他们号称文学,号称先锋。谁都知道,他们仅仅是伪流氓而已,所谓山中无文学,流氓称大爷。伪流氓已经若此,真流氓们来了之后,还有文学的活路么?文学恐只有如阿Q一般,低声倾诉,“革命革命”,最终定是革了自己的命。
我明白,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突如其来的强奸,它将会带来一层一层的高潮。
一位老学究告诉我——既然不能改变被强奸的事实,就享受它带来的快感吧!多么精辟的话语。从前我很尊重这位学究,现在更加尊重。他总是能顺应潮流,改变自己,不断地重塑自己的身段以适合这个时代的飞跃。他的高潮不断,一波接着一波。他享受,他承担。我想,我的纯洁,已经成为了我的耻辱……
我的一位道貌岸然实则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朋友告诉我,——颠覆是一场革命,既然你不能改变这个既定的事实,那么就努力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罢。然后他又做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怒其不争的模样来告诉我,——其实,革命真正的定义已经被莫名其妙的谬论所强奸。在这一刻,我开始觉着这个家伙才华洋溢了。我也明白,他已经脱离了伪流氓的阶层,真实的无以复加流氓的学富五车了。
一个编辑看上我一篇偶然为之的仿流氓文字,约我给他一篇真流氓的稿子。我努力了一个又一个地小时,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地我认为极其流氓的字眼,可是那位编辑依旧告诉我,“你丫太不流氓了。你要学会用身体写作。”我迷惑不解,“可是我是男人。”编辑同志大义凛然的告诉我,“男人怎么了?男人就不能用身体写作?现在已经是轰轰烈烈的男色时代了。”我恍然大悟,难怪葛红兵同学的《沙床》突如其来的袭击了我。但是我依旧不知道我那单薄的身体到底能当作多少本钱,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愿不要甘洒烫精写春秋。
暧昧一些,再暧昧一些,不会暧昧就赤裸一些,每个人都有机会。——酒酣耳热之后,前辈告诉我。——“一个大男人家的,还怕被强奸?可着劲儿享受吧,反正你也不损失什么。女人们都不再在乎牌坊,你个大老爷们还扭扭捏捏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作甚?”我恭恭敬敬的端起酒杯,一干而尽,再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只是担心精尽人亡。”前辈大笑,“汇源肾宝,保护你的肾。”刹那间恍惚,我越来越觉得眼前的前辈就是那个广告的主角。
文人何须怨流氓,春风不度玉门关。曾几何时,文学青年成了骂人的话,板砖一车一车的送给文学青年们。可恨的是文学青年还不会废物利用,板砖砸来也便随它去了,谁也不曾想到借着这免费的板砖造个世贸中心什么的,哪怕被拉登派架747撞了呢?流氓,多么高尚的词汇,高山仰止山外有山目不暇给绚烂多彩,一堆堆的溢美之词,流氓们忘乎所以的得意忘形,心下是骄傲的。于是放声大胆高呼,“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副舍我其谁天下独尊地派头!
斛箸交错之后,酒饱饭足之际,拍屁股走人之前,前辈又一次教导我,——真的怕精尽人亡的话,就选择强奸别人罢。
我呆立原地,强奸或者被强奸,这是个问题。如同A或者B,这是个问题。
石康说,——我就是晃晃悠悠也要向前冲,我就是支离破碎也要向前冲,我就是一塌糊涂也要向前冲。我明白了,于是,我就是分崩离析也要加入流氓的队伍中去。
既然无法做一个强奸的施加者,就努力的承受吧。A或者B,总归要选择。咬咬牙狠狠心,就是B了。只是,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么?千途万路于我,只得这这唯一的选择而已!不但选择,不但承受,还要学会享受。
·上一篇笑话:
大学生该有的修养
·下一篇笑话:
大话西游之中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