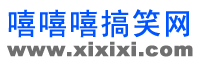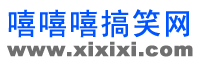当梁山打出“替天行道”旗号的时候,招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倘若天道不行,就会有“革命派”和“投降派”的争议,实质在于是革命还是改良,是颠覆还是修补。“替天行道”也有两种含义,一指带天行事,纠正无道偏差;二指以我为天,取无道而代之。若从字面上解释,这两种都解释的过去,差别是“天道”何在,由谁代表?或者说,对“天”的合理合法性有没有异议和置疑。
如果结论是天空仅被乌云遮盖,只要拨云见日,天下就会阳光普照。那正是宋江的政治理念,按水浒的话:“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这话的潜台词是:“体制是好的,但运作体制的人坏了。”套一句伟人的精辟评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宋江曾有豪言“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丈夫”之处是取而代之的私念,而他宋江则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偏狭想法,是光明磊落的,大公无私的,一心为国为民的。至于如何才能拨云见日,这尚未在他的算计之中。那是第二步的事。首要的乃是如何从为体制不容到融入体制。何况俗语不是也说了?“乌云遮不住太阳”。只要有一天皇帝忽然梦醒或被唤醒,重新焕发第二春就可以了。到水浒的最后一回,被奸臣毒杀的宋江曾魂邀徽宗梦游梁山泊,并倾诉冤情,弹劾奸贼,结果是冤得伸而仇不得报。“至圣至明”的天子仅仅认可了他的忠心。
在下倒不同意招安等同于投降,就宋江而言,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取得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均出于自保和为谈判赢得筹码,让朝廷不敢过于相逼,并非旗帜鲜明地反对体制,站到其对立面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叛和对抗何来投降?不过被怀柔,被安抚,被赦免,被收编而已,以前的冲突可当作一时气愤的过分举动,属“人民内部矛盾”,作些简化处理或一笔带过即可。
韩非子说过一个故事:楚人和氏有一天挖到了一块宝玉,拿去献给楚王,却被鉴定为顽石。楚王大怒,砍了他一条腿,后来这位楚王的儿子登基,和氏以为时机到了,又再度进献,结果又当成骗子,被砍掉了另一条腿。等儿子的儿子即第三代楚王上任之后,无腿可砍的和氏抱着那块宝玉哭了三天三夜,可谓惊天动地,第三代楚王派人前去询问:“不就是犯了错误受罚而已,为什么要如此大呼小叫,扰乱社会秩序?”和氏的回答耐人寻味:“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此话打动了君王,这块玉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流芳百世,被命名为“和氏之璧”。
宋江就好比楚人和氏,身怀忠君爱国的宝玉,却被视作叛逆谋反的顽石,想献给天子,竟屡遭挫折,颠沛流离,被迫走上了对抗体制的道路。不过献宝的愿望却一日未曾断绝。终于有一天这块玉被勉强接受了,可惜却不是因为宝玉的珍贵得到了认可,而是顽石的坚固难以撼动。如此一来,比之和氏,宋江的下场更为悲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虽深通权谋,狡诈多智,却始终放不开,舍不下一个忠臣梦。“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这句话用到宋江身上更为贴切。
宋江接受招安之后,手下有三五千人离开,但107条好汉中虽有不少人不甚赞同,却并无一个请辞。盖所谓“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他们和宋江是都被相同的道德观“忠义”所约束,有本质相同的信仰。“忠”是宋江心愿,“义”是好汉们的理念,宋江无条件尊奉体制,好汉们则无条件服从宋江,如果需要指责宋江的话,那么沦为帮凶的众好汉似乎也该负一份责任,或者说,也可算作和氏家族的传人。
不过也且慢就此责其“愚忠”,甚至贬之为“奴才”。宋江有武装而不谋对抗,好汉们有看法却仍然跟随,这与和氏有宝物却不私藏或图个高价,非要献给君王是出于同理。因为在和氏看来,只有君王才是宝物的归属所在,才配拥有宝物。这同一个虔诚信徒认定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或权威,满怀敬畏崇仰之心,甘愿付出一切的宗教效应是相通的。“相信”的力量就有如此强大。现代人就不会犯这种傻了?呵呵,也未见得。
·上一篇笑话:
孙悟空的工作报告
·下一篇笑话:
杜十娘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