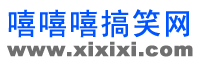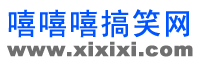一想起过去48小时里我的癫狂迷乱,我就惭愧到内伤。以我精神的强悍和永恒,面对肉体的软弱和短暂,居然理性之光只一闪而过,而把哭爹叫娘之声留给了整个漫漫长夜。
每年立秋后,五行转为金,躁热渐升。虽然我每年这时候催动内息,打通任督二脉,使体内毒火散诸三万六千毛孔,但在体表还是会形成疖子,很是痛痒一阵子。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疖子生尾椎,秋来发几颗。今年的疖子居然长到了尾椎上,一时不察,竟然发炎红肿,蔓延成姆指大小的一个硬块。
虽然我们的尾巴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本来有尾巴的地方依然神经丛密布,血管纵横。血气既已不畅,疼痛遂生。而这个部位又十分棘手,站姿血液下行,肿胀加剧,疼痛难忍;坐姿受周围组织挤压,椅上似有钢钉,一触即跳;只能卧倒,而且只能是俯卧,整日地俯卧。趴了48小时,我的胸肌都压平了。
我曾以为疼痛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慢慢减轻,我猜对了开头,但没有猜中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痛绵绵无绝期。每一次心跳,就像挨了一鞭。我整夜在床上移动身体的每一个零件,寻找一个最佳布局,使力量均匀地分配到周身。先是自动调节,然后是手动调节。先粗调,后微调。试了大半夜,终于得出了结果:无论怎么调,都疼。凌晨五点,无边的倦意战胜了疼痛,我昏死了过去。凌晨七点,伴随着又一阵的疼痛,我迎来了早晨第一缕曙光。
我决定去看医生,看就要看西医。白大褂,戴眼镜,操刀就像拿筷子一样。我要他给我一刀,连肉都挖了去。我宁可再忍受一个星期刀口的疼痛,也不要现在这种疼痛,哪怕多一秒。既然已经为难了我48小时,我们之间就已经爆发战争了,我要的是胜利,别怪我心狠手辣。
罗马式的柱子上是金字的匾,左手是长100米的收费处,右手的领药处100米长,中间的导医小姐和蔼可亲,凸凹有致。她对我说,你应该挂肿瘤科。我反问说:长个疖子就得看肿瘤科,那我腰围一米,是否应该去看产科?她的脸红于二月花。
外科门外是100个座位的候诊区,100个座位上坐了107个人。我拿着我的号,屁股扭来扭去,仰头看着显示屏上的号码,即使是古时放榜,也不过如此。要不怎么说人性本恶呢?在来苏水的味道里,在小孩的啼哭声中,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下,在看似无尽的等待中,我无数次在心里呐喊:为什么那么多人?!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对自己说:枪!很多很多的枪!我要把他们全突突了,就剩下我一个,我就不用再等待了。
女医生把我叫进5号诊室,听完情况介绍,只说了一个字:脱!零点零一秒,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主动在陌生女性面前脱下裤子,即使是技术娴熟的老流氓相形之下也会黯然失色。然后就是惊呼!再然后是就是沉默。在这沉默中她拿了小棍往肿块上戳,最后就是我的惨叫。
“给我一刀成吗?求你了!”我含着热泪问她。她睿智的目光穿透了眼镜,“不!你的疖子还没有化脓,没有出头,没有波纹反应。先给你抗生素,你再等两天。”我听到“两天”这个单词的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跳上去把她活活掐死,然后让110把我当场击毙,那么,一切都了了。
我哭着拿了300块的药单几乎是爬着逃离了医院,我得给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要他来救我。朋友放弃了抓坏人的工作,第一时间赶到了我的身边,他答应带我去看著名的中医师。
在一条妓女、小偷、杀人犯频繁出没的租房区,埋伏着著名中医胡青牛大夫。诊所不大,一窗一床一桂一桌一椅而已。白墙上满是题字,都是本地的文化名士的手墨,小篆、大篆、不大不小篆都有。无一例外,内容都是:He is the best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胡大夫喝了很长时间的茶,在一种近乎神秘的气氛中,他干枯的手穿越虚空,按在我了的腕上。我立即感觉到一道纯净的内气从我的脉门进入,澹澹然,汩汩焉,连绵不绝。此种内力相当精纯,一触便知这是正宗的武林名门内功心法,绝非江水湖水。
我刚要开口说话,他立即止住我,“不要说,你不要说,我全知道了。”我分辨道:“大夫,我。。。”他显然是动了真火,“我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朋友过来问给什么药,他自信地回答:青霉素。朋友又问是否皮试一下先?他迟疑了。朋友又说,美国的青霉素不需要皮试的。于是,他和我朋友谈了十五分钟药材的事。十五分钟以后,胡青牛大夫给我打了四瓶先锋。
其间,他写下了药方,从仓库里配好了各种草药,包成一大包。要我回家三碗水煎成一碗,最后五分钟放大黄一片。我问他不是说大黄有毒吗?他明显对这个“毒“字很敏感,道:“谁说的?怎么会有毒?”我立即背诵口诀:“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他什么都没说,收了我150元人民币。
入夜,我喝了中药,疼痛反而加剧了。我趴在沙发上,声声唉嚎,像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犬。其实,这条犬的问题并不在脊梁,而在尾巴。通过三个小时的哀嚎,我发觉唉嚎这种事还真让人上瘾。号着号着就停不下来了,而且似乎号一号,疼痛就能减轻一点。号啊号的就习惯了。
号毕,我又拿起了电话,去求我干妈救我。我的干妈是我好朋友的妈妈,好友去了香港,她就成为了我干妈。干妈是中医师,手段高超。但近几年来,很少有时间探望她老人家,而且问题出在尾巴上,不打好意思打搅她。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请出她老人家来,也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干妈叫我第二天一早去她的诊所,我出门的时候想了想,把胡子刮了,顺手梳了梳头。后来的事,如干妈回忆: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胖子能在秋风中抖成那个样子,她心疼坏了。我依然恳求干妈给我一刀,干妈犹豫了很久。说:那就得住院了。又问我有没有医保卡,我说单位办了三年,还没搞定。她一声长叹。干妈又对我说,即使有医保卡,她也不赞成我去开刀,因为除非是她亲自护理,其他人断然没有那么多心力随时维护伤口,很容易造成感染。
干妈在瞬间进入了沉思,沉思完毕就给我开了药方。当我看见马应龙麝香痔疮软膏的时候,我绝望了!我太年轻,还没来得及长男人必备的痔疮,而且我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痔疮!干妈给我解释了一通道理,她这人从我10岁就和我讲道理,我总相信她。我拿了药回到家,内服外擦,全套做完。
2小时后,疼痛消失了。我两天以来第一次安然睡去。干妈给我开了37块钱的药,全是些寻常药物。她说,未必效果就不如贵的,我信她。
我得出个结论:医生能医好病人,不是因为技术,是因为他的爱。没有一个医生能如我干妈一般地爱我,肯站在我的角度替我着想,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让我相信他如同相信我干妈那样自己去谨遵医嘱,因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如她一般把我治愈。
·上一篇笑话:
教语文乐翻天
·下一篇笑话:
各地大话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