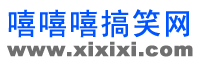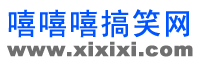那是下午,我带着个银白色的哨子到一个体育场看足球比赛,不经意间,就遇上了她。我这回在见到的所有“哨子”中间,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了。她一手捂着脸,仿佛很是羞愧;一手用刀拼命地刮着哨身,想露出点白来,却总是那么无济于事: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黑哨了。
我不由愕然,一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是的。”
“这正好。你是当老师的,读过很多书,知道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神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地切切地说,“一个本来是白色的哨子成了黑哨之后,究竟能不能恢复本来的面目?”
我呆住了。对于黑哨与否,我自己向来是十分愤恨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给她一点自信吧——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能够,又希望其不能够。然而我又何必增添烦恼人的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能够罢。
“也许能够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那么,也就没人会再吹黑哨了?”
“啊!再吹黑哨?”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再吹黑哨?——论理,就该不会。——然而也未必——谁会预料得到——”“那么,球迷们也就不会再继续对黑哨不满了?”
“唉唉,会不会不满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划,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能不能恢复本来面目,我也说不清。”
她看着我带着的银白色的哨子,说:“唉唉,要不是别人吹黑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
“我真不幸,真的。”她开始呜咽了,“我单知道我是一个哨子,在足球比赛中别人会很公平地吹哨,我不会有什么事情,谁知还是有人来吹黑哨,而且吹得很凶。我不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为什么竟会到了现在的地步?”
我趁她不再紧接地问,匆匆地逃离了体育场。
其实黑哨恢复本来面目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放在硝酸里边把黑的一层去掉,但它需要勇气的,因为太少的人可以忍受这种疼痛。只不过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不经历疼痛根除黑哨,那就放心等着别人来骂好了。
·上一篇笑话:
《大腕》老婆版
·下一篇笑话:
当冯小刚遇到了周星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