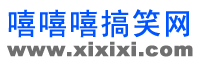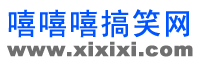如果要写她的一生,也许会很长。吕雉坐在她那华贵的宫殿里,琴声悠悠如水,长明灯在风中忽明忽亮,细密的脂粉已掩饰不了镜中女人日渐衰老的容颜。曾经,她也十分美丽过。现在已没有人再记得了,只有她自己还牢牢地记着。
虽然对于现在的她来说,美不美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世上,再没有一个人的尊荣可以超越她了。她朝着镜子笑了一下,那笑竟是有些狰狞的。她怔怔地有些悲凉,她想她老了。人老了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容易怀念过去。
也许哪日,该去趟沛县。也许在那里,她可以找到她早年的梦。
第一次遇见刘邦是在哪里?
并不是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
不是,在更早,早年的我很喜欢上街,因为我长得漂亮,我常常借故买东西在街上走来走去,可是我很少买东西。我喜欢看那些人用某种眼光打量我,那时候我常常会把胸挺得更高,把步子走得更加地妩媚。他们会朝着我吹口哨,那口哨是那么短促的一声,在空中那个转儿。那都是些在街头逛来逛去没事干的痞子,刘邦那时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眼睛总是比别人更加的赤裸裸,把我从头扫视到脚,我当作没注意到他那副好色相,但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是怎样在一件一件地剥着我的衣裳。我哼的一声,从他身边走过去了,他的眼光还滴溜溜地盯着我打转,这个流氓。
他长得怪怪的,高高的鼻子,长长的头颈,还特意留了长长的胡须,那胡须倒不赖,大概是他脸上最漂亮的部分了。那天我走过时,他正在与一群痞子在树荫下打狗骨头赌钱,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正抬起头来,我的目光被他捉住了,他一下子就到了我面前。“靓妹妹!”他喊我。我禁不住笑了下,那时我很爱笑,不象现在,现在我已经不知怎么才能如此自然地微笑了。
人要得到一样东西难免要失去另外一些东西。这已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有时是事情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前进,我只能变成这个样子,毫无办法。如果当年我嫁给的是当时沛县的王县长,那我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不过事情既已如此,假设又有何用呢。我还是继续回忆更好些,因为回忆是审视蜗牛爬过的轨迹,那些粘粘乎乎的白色凝固物,是怎样成年累月地积蓄着。而我又是有着那样鲜明记忆的人,无论翻到那一段,都是历历在目,欢笑也好,鲜血也好,那都是我。
下一刻我们已经坐在王媪的小酒馆里。这个酒馆在城西,从前我可从没来过这种地方。
“好脏啊。”我说。
“老板娘,来擦擦桌子!”刘邦大声地吆喝起来。
一个老女人从店堂里面跑出来,对着刘邦皱皱眉头,不胜其苦的样子:“怎么又是你,上次欠的酒钱还没给哦。”
“老规矩,年终结算。啧啧,什么态度,没见我今儿个有贵客吗?客气点,把最好的酒菜拿来!”刘邦大大喇喇地抱怨:“老板娘啊,你这地方啥时候该装修一下了,也象人家城东边弄得亮堂一点,弄俩儿唱小曲儿的来助助兴。”
“装你个头,你再不把欠的酒钱给补上,老娘我的店子都开不成了,还装修,亏你说得出。”
“还有这位贵小姐,可得当心着点。”她嘻嘻笑了两声,闪里面去了。
我心里有点掂量着如果这事传到我父母亲的耳朵里去,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狠狠地瞅他一眼:“显然你的名声并不好。”
“我不好?别听她胡扯,这老妈子更年期症候,见不得别人开心。你去打听一笑,我刘季可是大大的好人。”
那天我们喝酒喝得很痛快,我从未如此痛快地喝过酒,他东南海北地谈着,他去过很多地方,哪里的山好哪里的水好哪里供奉什么神他都能讲得绘声绘色,后来他先醉了,真奇怪,我却没有醉,我一生都没有醉过酒。我是个不会醉酒的女人,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显得不够可爱。
我曾经想努力做个可爱的女人,但做不到,我做了皇后以后不再有人爱我了,所以后来我只能做到让人怕我了,不能让人爱让人害怕也是好的。可是那时,在我年青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爱我的。
我们一开始并不住在沛县,我们总是把家搬来搬去,父亲在很多地方都有朋友。父亲他拿着一种测量仪,是一条龙嘴里含着个珠子不停地在转动,如果某一日停下来,把珠子吐出来的方位,就是指引我们前往的方向。于是我们一家离沛县越来越近,终于有一日,我们来到了沛县。我们开始在沛县建宅落户,沛县是一道起跑线,我开始我命运的马拉松赛跑。
父亲那么早以前就看出了我不可逆转的命运。无论走哪条道,都是通向一个目的地——富贵荣华。就象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未央宫的夜明珠照亮了大厅,音乐悠扬,吟咏诗人歌吟着我们伟大的战绩,歌颂着我超人的智慧。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浮光掠影,我比其他人更加懂得这一点。所以趁着我还拥有权势的时候,我最大限度地利用。谋略也不过一项游戏,而我只是想把游戏玩弄得更加精湛一点,毕竟,这是我仅有的一项爱好了。
我阴阴地笑着,宫里宫外的那些人在说些什么,我又怎会不知。谁不在说我心狠手辣,说就任由他们说去好了,他们又怎会知道我心头的痛与恨。如果我不能藉由这复仇的途径来发泄,那么也许我会疯掉,或者我早已是个疯子。可现在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曾经我也享受过美好的岁月。
家里的房子不久就造好了,有挂着秋千架的花园,有宽敞的门厅……我与哥哥们常在书房里读书讨论功课,父亲则常常与客人们坐在厅里讲谈天下大事。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他们指手划脚的样子。
这年,天下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在博浪沙一带将一大锤子掷向皇帝的座车,不料偏了,打在副车上。始皇帝虽则安然无恙,但天下却被搅动了。家家户户都清查人口,捉拿刺客。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原则,杀死了几千个疑犯,也没有把真正的刺客给捉到。多年以后我们遇到张良的时候,这个谜团才算解开。
可见冥冥之中,人都是有定数的。会与谁相遇,与谁错过,都有安排。
我再次看见刘邦时他骑在一匹马上,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旁边还跟了几个小喽罗。看见我,他停下马,吹一声口哨。
“嘿嘿……靓妞,咱们真是有缘啊,又遇上你了。”太阳有点强烈,他眯着眼瞅我。
曾经发誓不再见他,因为他与我们不是同一阶层的人。但是,天定的命运是无法违抗的,即使走在白茫茫无边无涯的旷野也无法躲避这种相遇。后来我又一次又一次地遇上他,在街角,在院墙外,在大树下,避无所避。他对我志在必得,不知是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还是因为我是我。多年以前我坚定地相信那是因为我自身的吸引力,今天我不得不对此感到疑问。而正是随着这种信念的消失,我对一切身边的人事都感到了怀疑,我不知谁会在明日里背叛我,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法相信了,那她还能相信谁呢,我就是这么来呢,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
在我还是个妙龄少女时,刘邦并不是唯一向我求婚的人,来我家求婚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我们家一个月内要换掉一根门槛。有人是因为我的美貌,有人因为我的聪慧,或因为我父亲的名气,又或因为我头顶上那顶缥缈的传说……综上所述,我便成为了抢手的热门货。后来我父亲的朋友本县王县长(他也同样对我虎视耽耽)利用职权把这些人暗暗修理了一顿,因此在几个月的喧哗之后家里又复归了平静。
那时我正为了保卫我的贞操与刘邦展开一场拉锯战,他思量着诱惑我的手段,我则寻找拒绝他的理由。我们比拚着耐心,看谁能支持到最后,看谁抢先气馁。这是日后楚汉战争的一场彩排。由小及大,两个人的战争与两个国家的战争也没多大区别。
我说我们之间埂着高墙,母亲曾说过找对象最好找门当户对的。刘邦说:世上没有越不过去的墙。他勤练跳高,他跳过的高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高度给他赢得了荣誉、女人以及享用不尽的金银财宝,最后他奄奄一息时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刘邦以一记漂亮的鱼跃龙门的姿势飞过我们家高高的院墙,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稳稳落地,宾客们大声地喝采。那天正好是我父亲的生日,我父亲老眼昏花,以为是天降神人,不禁也抚须叫好。上茶,看座。刘邦嘿嘿地笑着,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他赢得了我也就赢得了天下。
喜乐奏起来了,红绸子穿起来,我是新娘,他是新郎,我们结为了夫妻,行起了夫妻之事,我给他生了一儿一女。所有女人该做的事我都替他做了,我自信不曾对不起他,他后来却大大地对不起我。这事让我很窝火,如果我是个窝囊废我是个丑八怪那我也认了,可是老天生我却是聪明绝顶,我的姿色或许在岁月与怨恨中被逐渐消磨了,然而仇恨与智谋却在狭小的空间里越长越密。终于有一天,如火山爆发,岩浆喷涌而出。
如果可以,我宁愿不选择这样的生活,我更愿意我是个贤良的妻,得到丈夫的尊重与爱抚。可是没有人来听我的这项愿望,连上天也没有听见。他一次又一次赐于我失望,最后我连一点点的盼望也没了,最初的相遇是那镜花水月的泡影。人生如幻,我只是走了一遭,扮演了多重复杂的角色。或许,我是有实力去角逐历史最佳女配角奖。在这男人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女人是不可能成为主角的。我演的这出戏,也不过是为了陪衬出一个男人,他曾经是我前半生所有的希望。
后来这个希望破灭了。失去了依靠之后我不知该倒下还是该直立,倒下很容易,要站住却很难。我选择了后者,为此,我面临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的危机。但最戏剧性的却是第一次。
那是个春天,各色无名的野花在田野里开放。一口大锅在我身后沸腾着滚烫滚烫的水,我满怀希望,等着我的丈夫刘邦前来。他来了,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仰起头,一如以往。他与项羽开始对话,大多数话我忘了,但有几句我却印象深刻。项羽用剑抵住我说:“煮了她。”刘邦说:“好,吃了她。”……
他们开始商议怎样吃我,吃人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到处是哈哈的大笑声,夹着吃人的鼓噪的话题。我神色从容地坐着,我的口中正徐徐吐出醉人的浓香,我极欲开放。
·上一篇笑话:
别惧怕手机
·下一篇笑话:
神仙的牲口